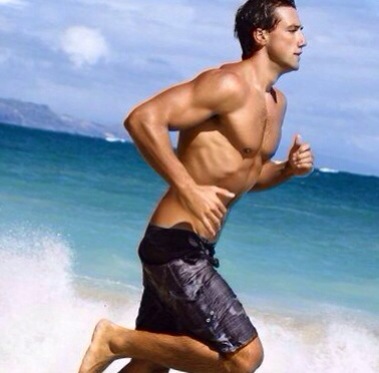分享
比尔.盖茨:什么是乐观?
比尔.盖茨每年底都会记下当年最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好事。对于 2014,他列出的好事包括:连续 42 年,儿童死亡率下降;年新增艾滋病感染后接受治疗人数,超过年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;轮状病毒疫苗被更多孩子使用;新结核病治疗方案获得突破;尼日利亚对小儿麻痹症的抗争帮他们抗击了伊波拉病毒。以下公开资料,来自盖茨和其夫人梅琳达去年在斯坦福的演讲,有关科技创新最终为什么服务,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乐观。
能受邀到斯坦福做毕业演讲,对任何人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,我们尤其如此。斯坦福是个盛产天才的地方,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,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概括,我们最爱斯坦福的一点,是“乐观”。
这里有浓郁氛围,让人觉得创新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也正是这种信念,让我在 1975 年离开波士顿郊外那所大学,并永远辍学。我相信,神奇的计算机和软件会帮助各地人,让世界更美好,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40 年,我和梅琳达结婚也已经 20 年,我们比以往更乐观,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我们学到的,你我的乐观将如何帮助他人。
我和 Paul Allen 创建微软时,想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带给人们。当时,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计算机,我们希望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份力量,使计算机民主化,到 1990 年代底,我们看到个人计算机对人的巨大效用,但这种成功,产生了新的困境。
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计算机,而穷人不能,这种技术将加剧不平等,这与我们的核心信念相抵触,因次我们努力缩小差距。我把它当作微软首要任务,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的首要目标,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,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。
1997 年时,“数字鸿沟”引起我的关注,我首次去南非出差,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中,当时距 Nelson Mandela 上台只有三年,种族隔离刚刚终结,我同主人共进晚餐,主人用红铃唤来管家,餐后女人会和男人分开,男人们开始抽雪茄,我心想,幸好我读过简·奥斯汀的书,不然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第二天,我到索韦托,约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贫穷小镇,也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。从城区到小镇非常近,而入口却如此突然而刺眼,我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索韦托之行,让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无知,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,和我们在美国做的一样,但我很快明白,这里不是美国。
我见过关于贫穷的统计,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,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铁皮屋里,没有电,没有水,没有厕所,大多数人不穿鞋,在街上赤足行走,不过,那里没有街道,只有布满车印的泥路。
社区中心没有持续电力供应设施,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,从社区中心链接到 200 米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,看到装置后,我明白:一旦记者离开,发电机会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,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会离开这里,为不能被电脑解决的问题担忧。
当我对媒体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,我说:“索韦托是个里程碑,我们正面临的重大决定是,科技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落后,也就是要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。”但当我读出这些词,我却发现它们关系其实不大。
当时我没说的话是:我们并没注意到一个事实,这块土地上,每年约有 50 万人死于疟疾。在我前去索韦托前,我自以为理解世界的问题,但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视而不见,我如此震惊于所见,并因此扪心自问:我还会相信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吗?我对自己保证,在重回非洲前,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困的原因。
这些年来,梅琳达和我发现了更多贫困者的当务之需。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,我来到一家医院,探访 MDR-TB (抗药性结核病)患者,或叫耐多药结核病,一种治愈率不到 50% 的疾病。
我还记得这家医院,一个绝望之地,巨大的开阔式病房中,无数病人拖着脚步,穿着长衣,戴着口罩,有一层楼专为儿童开设,包括一些床上的婴儿,这有一家很小的学校,让适龄儿童学习,而很多孩子却撑不到那个时候,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。
我同一位 30 多岁的病人聊过,她曾是结核病医院一名职工,因咳嗽病倒。她看了医生,医生说她患上耐多药结核病,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,她活不了多久了,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床位,这是一个有着排队表的地狱。但见到地狱,不会减少我的乐观,它指引乐观。
离开时,我坐进车里,告诉医生我们的身份,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很难治,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。实际上今年,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个阶段,对那些病人,他们不需再为 18 个月 50% 的治愈率花费 2000 美金,只需为 6 个月 80% 的治愈率花费不到 100 美金。乐观常被视作为错误的希望,但错误的绝望也存在着,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时的这种态度,实际上,我们当然能。
(梅琳达):比尔造访结核病后给我打了电话,一般来说,如果是国际旅行,我们会核对当天行程,但这通电话不一样,比尔说:“梅琳达,我到了从未去过的地方。”之后,他哽咽了,说不下去,最后他只说了句:“回家再告诉你吧。”
我知道他在经历着什么,因为当你见到毫无希望的人时,它会让你悲痛,但如果你想做得更多,你就得见到最糟糕的真相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日。
大约十年前,我和一群朋友到印度,在那最后一天,我见了一群妓女。我想和她们谈谈她们面对的艾滋病的危险,但她们想告诉我的是她们的污点,这里很多妇女被丈夫遗弃,这就是为何她们开始卖淫,她们想养活自己孩子,她们在社会眼中如此卑微,以至可能会被任何人强暴,甚至警察,但没人关心这些。
与她们谈生活对我触动极深,但我印象最深的是,她们多想触碰他人,这种身体接触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,因此,在我离开前,我们手拉手拍了照片。
那天晚些时候,我来到一个印度的弥留者之家,我走入屋内,见到无数排病床,每个病床都有人照料,除了角落里那个。这名病人是一位 30 多岁的女性,我记得她的眼睛,硕大、棕色,流露悲痛,她如此瘦弱,徘徊在死亡边缘,她的内脏什么也盛不下,护士门于是在床下放了一个盆,在床中弄出一个洞,她身体内的一切就直接倾入下面盆中。
我看得出她患有艾滋病。艾滋病声名狼藉,尤其对女性,其惩罚就是流落一人,当我到她的床边时,突然感到完全无助,我什么也帮不了她。我知道我救不了她,但我不想让她孤独,因此,我跪在她身边,伸出手,她摸索到我的手,紧紧握住,不肯放开。我不会说她的语言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,最后只说了一句,“会没事的,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陪她一段时间后,她开始指着屋顶,很明显,她想上去看看,我意识到太阳要落山了,她想到屋顶上看日落,房间里的护士十分忙碌,我和他们说:“能把她抬到屋顶吗?”他们说:“不行,我们还得发放药物。”
最后,我把这位女士抱了起来,她已经瘦骨如柴,我带她来到屋顶,找来一个破旧不堪的塑料凳,把凳子放下,让她坐下,在她腿上搭了条毯子,她朝西面坐好,面向落日。我告诉护士们她在上面,让她们晚上日落后把她搬下来,然后我不得不离开。
面对这位女士的离去,我感到完全无能为力。而有时,正是这些你无法帮助的人,给你的启迪最深刻,我知道早晨见到的这些妓女,可能会成为晚上抬着的这名女士,除非我们能找到对抗羁绊她们一生“污点”的方式。
过去十年,我们基金会帮助性工作者,建立互助团体,让她们互相激励大胆说出话,要求安全性行为,让客户带上安全套,她们无畏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的低艾滋病感染率,很多研究表明,关于艾滋病为何未在印度大规模爆发,这是一个重要原因,而当这些性工作者聚集一起阻止艾滋病传染时,某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。
她们组建的社区,成了一切的平台,强奸、抢劫她们的警察和其他人,不再无法无天,这些女性建立起互相鼓励节省的系统,有了这些钱,她们可以离开性行业,这都是社会眼中最下等的人所做出的。
所以乐观于我而言,不是消极地期待事情变好,在我看来,这是一种信念,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好,因此无论我们目睹多少痛苦,无论多糟糕,我们能伸出援手,如果我们不失去希望,如果我们不转头而去。
(比尔.盖茨):梅琳达和我,都讲诉了灾难性的场景,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,即使在绝境之中,乐观会加速创新,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,但如果你从未看过遭受痛苦的人,你的乐观不会有用。你永不会改变世界。
这让我想到我眼中的一个悖论。现代世界是创新不断的源头,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,创立新公司,有思想的学校,硕果累累的教授,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,神奇药物,还有优秀毕业生,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,还是在深沟中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,你都在为人类见相互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。
但与此同时,如果你问全美国人,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?大多数会说“不”,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孩子或自己更好,那么,究竟谁是对的呢?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,让世界更好的;还是目睹不平衡趋势,及机遇减少且不指望创新带来改变的?
在我看来,悲观者错了,但他们不疯狂,如果创新完全由市场驱使,如果不关注巨大的不平等,那么我们催生出的惊人发明,将让世界分化得更剧烈,我们无法改善公立学校,无法治愈疟疾,无法终结贫困,不会做出发明,让贫困农民在变化气候中种出食物。
如果我们的乐观并未指出问题,那么我们的乐观需要同情心,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,我们会看到贫困、疾病与破败的学校,我们会以创新作答,让悲观者惊讶。
在下一代中,你们这些斯坦福的毕业生,会引领新一波创新的浪潮,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?如果你们的世界很宽,就会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,如果你们世界很窄,则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。
我从索韦托开始学到,如果我们想让乐观关系于所有人,赋予各地人以权利,我们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。
如果我们有乐观,却没同情心,那么掌握多少科学奥秘都没用,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,而只是在解谜。我想,你们大多数人的视野比我当时更宽广,在这方面,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,如果你们能全身心投身于此,我们对此迫不及待。
(梅琳达):让你们的心为之而碎,这会改变你们处理乐观的方式。在一次去南亚的旅行中,我见到一名穷困潦倒的印度妇女,她有两个孩子,求我把孩子带走,当我请求她原谅时,她说,那么请至少带走一个吧。
另一次去洛杉矶南部,我见到一群穷困社区来的学生,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,你是否觉得我们就是那群孩子?父母逃避责任,我们只是残羹剩饭。这些女性令我心碎。
当我对自己承认,这可能是我,同情心就更甚,我与旅途中遇到的母亲对话时发现,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什么不同,唯一差别在,我们将其给予孩子的能力。那么,差距何在?
比尔与我同孩子在餐桌上讨论过这些,比尔工作很努力,他冒过风险,为成功做出牺牲,但是还有一个他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,那就是运气,完完全全的运气。
你在何时出生,你的父母是谁?你在哪里长大?没有谁值得这些事,这些事务被赋予我们,因此,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,并思量如果没它们,我们会如何?这个人就会更容易看到贫穷者,并说这可能会是我,这就是同情心。
同情心抹平障碍,为乐观敞开新的大门,这就是我们想和你们说的,当你们离开斯坦福,带着你们的天分、乐观及同情心,改变这个世界,让千百万人为之乐观。你不需要着急,你还要开创事业,付清债款,找到并结下合适的另一半,现在做这些就足够,但在你的生命之中,可能你自己并未计划过,你会看到让你心碎的苦楚,而当这发生时,不要掩面而去,就在这一刻,改变孕育发生。
本文由 相聚福冈 作者:janson 发表,转载请注明来源!